为藏区“幸福路”站岗,有我
海拔5130米的东达山山顶,深夜的温度已经降至零度以下,坐在车里可以听到风的咆哮声和机器的轰鸣声。在车灯的照射下,只能看到官兵隐隐绰绰的影子。部分道路被毁,官兵们只能连夜抢修,力争减少对道路交通的影响。这只是官兵们抢修道路的一个缩影。
骨折的骨头从里向外刺到右大腿的皮肤表面,只在皮肤上留下针眼大小的伤口。“扎破皮的那根骨头像根针一样细,断成了不规则的形状。距离腿上的大动脉只有两毫米。”这是2008年,二支队机械操作手舒春宏在清理路面时所经历的。
路基不稳,装载机带着舒春宏翻滚下山。在山下100米的地方,舒春宏被甩出装载机。“我们就看到他坐在乱石滩上,抱着自己的右大腿,不说话,眼神一直看着很远的地方,也不知道在看什么。”当时还是通讯员的周伟回忆说。
“他说腿动不了了,有点痛。(我们)没有办法就把裤子用老虎钳扯了一个口子,把裤子撕烂。整个腿上只有一个针眼大小的伤口,一点血。我们一摸感觉有点扎手,像针一样。”
在这次事故中,和舒春宏同样被甩出装载机的还有指导员。由于伤势严重,指导员在这次事故中牺牲,只有30岁。川藏线交通大动脉的畅通凝聚着官兵的牺牲与奉献。支队组建以来,先后有15名官兵英勇献身。
通麦路段作为川藏线公路的一段,曾被称为“通麦天险”。如今,随着这一路段道路修缮、隧道打通以及通麦特大桥的通车,天险已不存在。
在通麦特大桥还未建成通车之前,通麦大桥就是越过易贡藏布江的唯一通道。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武警交通二支队九中队战士毕长春和通麦大桥的关系,那一定是“战友”。这座桥“守”着川藏线,毕长春就守着这座桥。
2009年12月,毕长春来到通麦天险,成为守桥班的一员。一直到2016年通麦特大桥建成通车,毕长春和他的战友守了7年桥。由于通麦大桥是一座钢筋桥,承重能力有限,每次只允许单方向通行,并且货车的载重量不能超过20吨。
在这座全长258米的通麦大桥上,毕长春和他的战友们每天都要检查大桥的吊杆、锚索、销子、面板等,确保桥梁安全。此外,他们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对过桥的大货车检查,以防超出大桥的承重量。
据介绍,每天至少有1000台大小车辆经过,大多都要向守桥官兵们发出一声鸣笛表示敬意。每一次车辆通过时,毕长春和战友们也要半面向右转腿敬礼,迎接汽车,表示可以安全通过。最多的时候,毕长春一天转腿达240多次。现在有了通麦特大桥,战士们不用再守着桥、对来往的车辆进行检查。但是毕长春空闲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还是“遛桥”,检查桥的零部件。

武警交通二支队四中队中队长舒绍芬和妻子卢文玲。中国青年网记者 张炎良摄
追到天边边 陪你站岗
“爸爸,你去不去我家玩?”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的作业又不会做了。”
“我的爸爸在天边,而我来到天边,看到的却还是天,爸爸你永远都那么忙,就连陪我都好像静不下心来。不过老师讲,你们是最辛苦,也是最伟大的,长大了,我也想去西藏当兵。”
四中队莫未已经驻守在“天路72拐”沿线将近9年。中队进行路面养护的时候,经常会有附近村子的孩子过来看他们。“他们现在都长大了。从五六岁的时候(他们)就跟在我们后面,现在都已经十几岁了。”莫未提到陪伴他们的孩子的时候,满脸笑意。
在祖国、人民面前可以挺起腰杆,提到自己孩子却能愧疚地红了眼眶。33岁的朱伟已经陪伴着川藏公路14年。有一次朱伟休假回家,带着5岁的儿子到公园玩。和朱伟玩熟了以后,儿子说:“爸爸,你去不去我家玩。”说到这的时候,这个被高原阳光晒得皮肤黝黑的军人,眼中泛出了点点泪光。
“他有他的理想,考虑了一下,所以我来了。”30出头的卢文玲辞掉了公务员的工作,来到四中队,和丈夫舒绍芬一起守望川藏线。妻子来探亲,舒绍芬还是不能停下自己的工作。舒绍芬每天去72拐路段养护公路,卢文玲就每天跟着中队的车去送午饭。等送到手里,饭菜差不多也凉了。“结婚两年半见了两三次面。能在一起还是很幸福的。虽然这里很艰苦,可能是因为他在这里,我觉得西藏挺美的。嫁给当兵的一点都不后悔,挺幸福的。”
欢迎拨打中国青年网新闻热线010-57380651或发送新闻线索至邮箱youthpress@126.com;关注“细腰蜂”(ID:beeyouth)微信公众号,可直接对话记者,曝料线索;关注“学习者”(ID:youth_xuexi)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学习动向。
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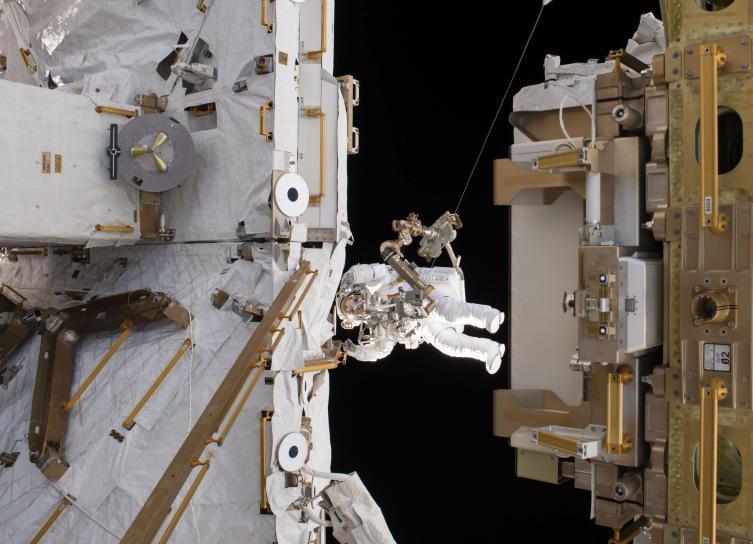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07246
京公网安备110105007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