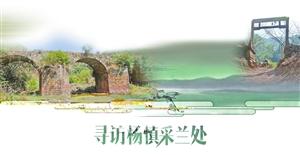 |
| 本报美编 杨千红 制图 |
李成生
密林深处,朝云暮霭,驿道如丝,莽莽苍苍的群山,渐行渐远,渐远渐淡,幻化远天。
这里是滇中古驿道上的一个关隘,陡峭悬崖下,一座石桥飞渡涧水,桥两岸由石级铺成的驿道,像一根橙色的线,将两座悬崖缝在一起。
这就是响水关。
响水关的东面是距禄丰县城15公里的南平关,而它的西面,关隘重重,有一个地方,至今牵动云南人的日常生活:一平浪盐厂。盐,这种被称为“百味之首”的矿物质,基本上就是脚下这条古驿道的历史,这种清代以前被国家直接控制的物资,在这条有上千年历史的古道上唱着主角,演出无数悲欢离合大戏。
500年前,有一个倒霉的才子路过这个关隘,见松柏苍茂,关山万里;闻鸟语悲催,涧水轰鸣。蓦然间,看到路旁悄然盛开的兰花,诗兴袭来,写下了一首《采兰引》。在诗序中他说:“广通县响水关产兰,绿叶紫茎,春华秋馥,盖楚骚所称纫佩之兰也,人家盆植如蒲萱者,盖兰之别种,曰荪与芷耳。时川姜子采以赠余,知九畹之受诬千古,一旦而雪,作采兰引。”其诗曰:秋风众草歇,丛兰扬其香。绿叶与紫茎,猗猗山中阳。给根不当户,无人自芬芳。密林交相翳,鸣泉何汤汤。欲采往无路,跼步愁褰裳。美人驰日成,要子以黄昏。山谷岁复晚,修佩为谁长?采芳者何人?荪芷共升堂。徒令楚老惜,坐使宣尼伤。感此兴中怀,弦琴不成章。
写这首《采兰引》的人,就是明代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这个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的状元郎,在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因“议大礼”、哭宫门之举而两次被廷杖,几至送命。同年底,被谪永戍永昌(今保山),大半生在云南度过。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生于明弘治元年(公元 1488年),卒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从风华正茂的五品京官到罪服加身的流放者,从天下闻名的才子状元到为天子所弃的戴罪平民,从前程似锦到一生漂泊无定、最终客死他乡,杨升庵的人生可谓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在这首诗中,不难看出他远离异乡的苦闷心情,以九畹之兰、生于荒野、不被赏识自况。九畹,就是屈原故乡的九畹溪,盛产兰草,后此词专属屈原。
我们无法考证杨慎的诗具体作于哪一年哪一月,也不知道他是第几次过响水关写下此诗的。但无可怀疑的是,此诗一创作出来,立刻受到文人骚客的追捧,和诗者众,而且,连关名都被改了,称为“兰谷关”。从中得知杨慎在云南文化界的巨大影响。
当时,兰谷关属广通县。杨状元说到的那个川姜子,可能是他的挚友吧?那时,从成都入滇的驿道(官道)有两条,一是秦时开凿的石门道(宜宾过盐津石门关入昭通、过曲靖到昆明),秦汉时称“五尺道”;二是经雅安过清溪关、嶲州(四川西昌)、永仁入云南的“清溪关道”。如果要去滇西保山,两条道在现在的南华县或祥云县交汇。过兰谷关,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从昆明去大理,要么从大理到昆明。显然,状元郎写诗时走的是昆明到滇西的驿道。从元代开始,南中(四川、云南、贵州一部)的食盐开采已经是官营,明清时,昆明到滇西的崇山峻岭中开辟了相当于现在高速公路概念的驿道,不少学者将其称为“茶马古道”。这个名字如果加予产茶的滇西南地区,一点也不错,但地处滇中的楚雄州,将其称为“盐马古道”更确切。
从昆明到大理,有一条固定的官道,那就是迤西古道(此处的“道”不指三迤行政区划),这一段路民间称有“九关十八铺”,新中国成立后的禄丰县占其五关。除昆明碧鸡关外,依次为:老鸦关(土官)、炼象关(腰站)、南平关(禄丰)、响水关(舍资)、回蹬关(广通),附关还有羊毛关、照普关。这一条路过沙却馆(南华沙桥)入大理境,是省会城市昆明至大理的必经之路。写诗的杨状元,走的正是这条路。
可以肯定,杨慎多次走过这条官道。史载杨慎多次往返于保山与昆明之间,访友赋诗,留下无数的佳作。
在距兰谷关不远的六里箐,杨慎写下一首名为《六里箐》的五言诗:“六里箐何深,千章树如齐。俯听秋蝉鸣,翻观幽涧底。涧水何湔湔,谷兰香靡靡。不见采兰人,谁为枕流子。日暮心悠哉,临风聊记徙。”因为是“聊记”之作,也就是记录一下沿途见闻,诗写得很一般,也许是骑在马上随口吟咏。可是有一首在当时被云南文人们交口称赞、广为流传的诗,却与禄丰有关,这首诗就是写于南华苴力铺的《垂柳篇》。
旧志载,有一个从福建来云南的巡按御史、名邓濮的人,有一次路过舍资驿,见墙上有杨慎的亲笔题诗,这首“作于苴力,题于舍资”的“自怀之词”,令这位邓大人“从壁间读而悲之”,于是作了一首《伤杨柳》,对杨状元的际遇作了一番喟叹。
其实,杨状元在响水关还留下另一首名为《兰谷关》的七言诗,其诗云:响水关水绕兰谷,兰之猗猗环谷芳。瑶汤玉氵巽 涌神瀵,绿叶紫茎含帝浆。湘累采作美人佩,尼父嗟为王者香。怀哉千古两不见,独立苍茫愁大荒。
诗前小序说:“原名响水关,因余采兰诗,时人改此。”由此说明,这首诗是杨慎重走此关后作。诗意虽与《采兰引》有相近之处,但诗人怀才不遇、贬谪边地的凄楚孤独感更甚,发出“独立苍茫愁大荒”的感叹。
在云南,在滇西到昆明的古驿道上,在禄丰五关的路途中、驿站、府衙间,万里贬谪的杨用修和云南的官员、文人骚客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个名动全国的大才子,受到云南官员和百姓的爱戴,文人们和他见上一面,是一种非常荣幸之事。
康熙《广通县志》记载,路睑(广通)是杨慎常往返的地方,因此在此“多题咏”。他和稍晚一些的李元阳等人关系很好,常在一起饮酒赋诗,此地的仙羊庵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明代大学者李贽也常往来于广通,“以仙羊聚圣堂为行馆”,并时不时在此讲学,许多广通的学子都聆听过他的演讲,他旷达的议论,令后学和官员们难以忘怀。李贽离开云南后,广通的朋友一直很怀念他,常去仙阳庵聚会,缅怀这位学问高深,人品皎洁的大才。
没有经历过响水关的徒步,很难理解杨慎写《采兰引》的心境。
仲春,沿南平关一路溯着古道,在密林中艰难穿行,两小时后,就在一个山口后面听到轰然的水流声。在经过六里箐时,怪鸟悲鸣,蝉声彻谷,细雨飘零;摇摇欲坠的关门虽在,但已苍苔覆盖,枯藤缠绕。依稀有苗族人在故关上耕种,几匹老牛闲适地在田埂上吃草,驿道绕村边而下,数百级石板铺成的驿道残破不堪,逶迤延伸到古旧但巍然屹立的古桥前。对面,石级旋盘崖上,兰花盛开路旁杂树草丛中。这种在城市中金贵得令人咋舌的野草,在这里却成片怒放,娇艳荒野。怪不得杨慎说“无人自芬芳”。
《孔子家语》有这样一段记载: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这是孔子回答子路的一段话,当时孔子被围困,断粮七日。孔子以兰的特性和生长习性,来比喻自己不因贫穷而动摇志向,也不因得失荣辱而改变信念。兰,多生长在溪边、原野湿地和湿润的山野林间。这一生长习性,使得它大多远离俗世,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不像桃花等较为常见的花卉容易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且,兰的叶虽经风霜而常绿,姿态高雅别致,气味幽香静谧。它不与群芳争艳,就算是无人欣赏,也含苞而放,芳香四溢。从兰的身上,可以看到隐士的气质、君子的风范,看到高洁、隐逸、与世无争的品质。屈原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吟唱着兰。在他的笔下,兰是君子,德行高洁。《离骚》中他写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王逸章句言:“行清洁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屈原的扈与纫,显示了自己德行高洁、修身清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格。他写“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虽然被流放,但还是种植兰惠等香草,明写兰惠,实际上是写自己的品行,虽然在流放中,但依然修行仁义,勤身自勉,朝朝暮暮不曾懈怠。他写“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行走时也要靠近长满兰椒的地方,以此说明自己时时刻刻不忘高洁。
难道,当时路过响水关、见野发幽兰的杨慎,不是如此心境?
如是,当时追随杨慎者众,不乏官员,令现代追名逐利、趋炎附势者汗颜。
明代山阴人张深赞道:“琼姿寒不死,清魂久愈卓”“荪芷经岁荣,过时有余绿”。县令李铨作《兰谷》诗,其序云:“广通县邑东兰谷,旧名响水关,因升庵采兰,遂更名兰谷关。其产兰,绿叶红茎,春华秋馥,升庵谓即楚骚所称纫佩之兰,赋诗志怀,盖自伤也。余吏兹地,幸治芳馨,用和短篇,敢云千载知己?志一时向往云耳。”并在诗中赞道:“绝域无人采,芳芗千载扬”。时楚雄知府冯甦(sū)说:“漫向边关悲弃掷,古来词客拌穷荒。”穷者见性,穷途见诗,自古皆然。
迤西大道,不是一条寻常的路。它有兰的馨香,有烈日的曝晒,有风霜的侵染;有荫翳的森林,有奇险的雄关;有崎岖的山道,有怒放的花朵;有出没的豺狼,有悲壮的故事;有怆然的喟叹,有睿智的思想……走过这条羊肠百折的路,可发幽古之情,可悟时间倏忽,顿觉时间之旷远,人生之短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