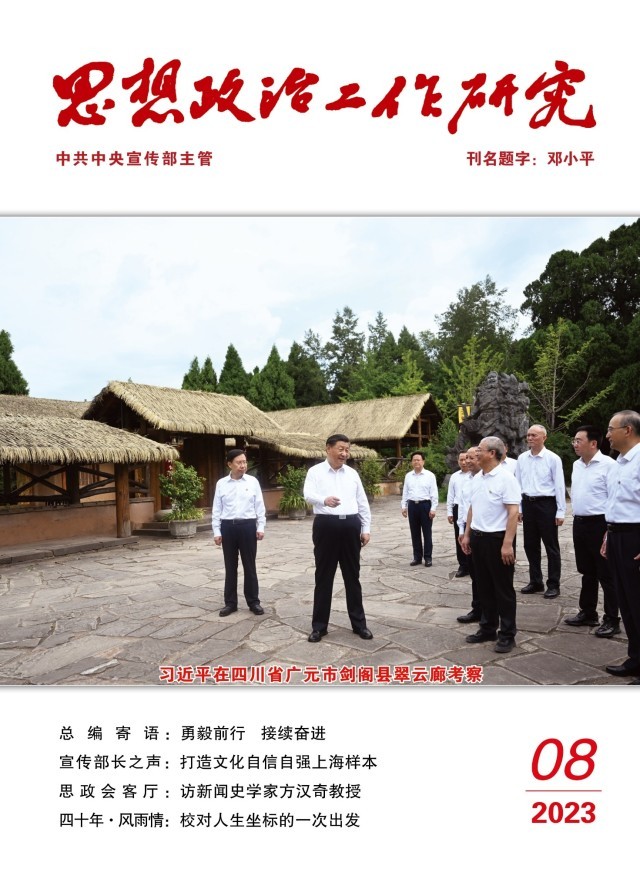
我的父亲张立志,山东省莒县小店乡人,1919年出生。他1939年任抗日自卫队指导员,194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没有令人仰慕的赫赫战功,也不是令人向往的大官,他是成千上万名为了革命事业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士兵中的一员。
年少时,父亲对我们很严厉,在家中轻易不表态,但说出来,就掷地有声。
1962年9月1日,我上学了。开学第一天,我斜背着书包,双手抱着一个小板凳,父亲推着自行车送我去学校,自行车的后座驮着写有我家住址和我名字的方凳。我第一次走进学校,又小又窄又旧的校门,泥路泥地凹凸不平,教室又小又暗,书桌是家里带来的,黑板是裂的,一写字就晃,厕所是南方农村那种前置竖板的,不小心就会掉下去。我以为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的,毫无介意。但我每天上学看到后院和周围院落的小朋友都往西走,唯独我一人孤单地逆着他们往东走,就想跟父亲说:要转学到西边小朋友们上的学校。但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不敢讲。
两年后的一天,父亲出差时,他单位的一位叔叔为我转入了西边的西湖小学。学校里,宽阔的校园、明亮的教室,木地板、铁桌椅、一面墙的大黑板,文体设施一一俱全。这时候我才慢慢知道,父亲带我上的学校,是旧庙附属房改的平民小学,西湖小学是干部子弟为主的学校。
严厉的父亲常常也是很慈爱的。小时候,我怕他,又想和他在一起。每天傍晚一到下班时间,我和妹妹们就会在院门口等着父亲回家,他出差,我们就掰着手指盼他回家。我们不知道也从没想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就知道他回来会给我们买来水果,会给我们钉鞋掌。除去雨鞋,我们姐妹穿的鞋都是山东老家寄来的手纳布底鞋。正是蹦蹦跳跳的年龄,这种鞋没几天就“穿帮露馅”。星期天,父亲会用自购的工具、自行车旧轮胎为我们钉鞋掌。每到这时,我们就围在旁边递剪刀、找钉子、拿榔头,不亦乐乎。这时我会向父亲告状,某某同学说,我的鞋“嘎土的”(杭州话很土之意),难看死了;后院的某某讥笑我:你爸妈真小气,鞋都舍不得买……听了我的话,父亲放下手里的活,说:“他们不懂!这个鞋哪是能买得来的?你爸爸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没鞋穿,大娘大婶们没日没夜地做军鞋,给八路军游击队穿,穿了这军鞋打游击,鬼子抓不到。现在鬼子打跑了,老家乡亲们给你们寄来鞋,让你们穿着她们做的鞋,不要忘本。”父亲的话,让我感觉自己赢了同学。
我家三姐妹,除了老大能穿新衣服,老二老三不是捡老大穿不了的穿,就是父母穿不了的让外婆改了给我们穿。我是穿着沂蒙老乡做的土鞋走进部队的,生活朴素的习惯,一直伴随到今天。
参军是我从小梦寐以求的理想。1970年底内部招兵,父亲不让我去,高中毕业,把我送回山东老家下乡。同学和老师得知我要去穷山沟,很惊讶。我们这届高中生是“文革”复课后的第一届,人数很少,即使下乡,也都在杭州郊区,与沂蒙山区比,条件好太多。把我从小带大的外婆知道后,更是伤心得泪流不止。其实父亲并不是铁石心肠,他太了解家乡的苦。
下乡的前一天晚上,父亲让我看了他的枪伤,这是战争年代留下的枪伤,我却是第一次知道。第二天要远离这个温暖的家,我心情很乱,就没有追问。让我纳闷的是,父亲叮嘱我让我平时要和老党员、“老妈妈”(老妈妈是山东家乡的方言,大妈之意)们多在一起。
第二天,父亲送我到火车站,火车启动离开站台时,我看到父亲把头别过去了。后来听我妈妈说,那一夜父亲翻来覆去没睡着,她是第一次看到我父亲流泪。
坐在北上的列车上,我心中的离情伴随着眼中的泪水,想起昨夜父亲送给我的1张泛黄照片和3张北海币。照片是父亲1944年11月莒县战役后在莒县县城南关照的,是他平生照的第一张照片。照片中共4人,有两人照完相后不久就牺牲了。北海币是抗战期间,我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发行的主币。发行北海币的北海银行就驻在父亲老家莒县桑园柏庄。父亲在异常艰苦中,把省下的3张北海币留存了下来,作为历史见证。这时又把它交给即将踏上人生之路的女儿,让她沿着他的来时路,去追寻他们那代人的理想信仰。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莒县,全城一条土路,一间点着煤油灯的百货店,县政府院里的办公室是没有天花板的半茅屋。我落户的村子,是抗战时期父亲与他的战友一起开辟的游击区,不通水电,猪圈是厕所,吃的是难以下咽、又硬又黑的地瓜煎饼,睡的是高粱秸秆编的硌人的床。从江南鱼米之乡到陌生的穷乡僻壤,这个落差对我而言,太大太大了!
我哭着给父亲写信。父亲也不放心雏燕孤飞的我,专门请假来看我。他带我走村串巷熟悉环境,带我去看望抗战时的老模范、老党员、堡垒户。在山里坑坑洼洼的羊肠小道上,我气喘吁吁地跟着大步流星走在前面的父亲,看着他的背影,我心里很不满,老大远地来看我,应该带我到县领导那里去,到山沟里来看这看那,有什么用啊?坐在脏兮兮黑乎乎的老乡屋子里,我浑身不自在,可父亲就像见了亲爹娘似的拉呱拉个没完。父亲看出我的态度,耐心跟我讲,他负伤时是民兵和老百姓轮流抬着他连跑带走3个多小时送到军区医院,是老百姓救了他。当年没有老百姓的掩护,没有老百姓的支持,他怎么会有今天,又怎么会有我!
父亲走了,父亲和老百姓之间的真情实感触动了我,我不能给父亲丢脸,努力接近这些喊我“闺女”的大娘大爷们,跟着男劳力抗旱、抢收……乡亲们给我送来最精贵的小米、白面,还有自家树上的水果,他们跟我讲当年父亲打鬼子、除汉奸,讲当年父亲给乡亲们组织识字班、做军鞋、送军粮……慢慢地,我感受到了乡亲们的淳朴和善良。在他们的关爱下,我渡过了生活关、劳动关。我熟悉了故乡的山,那里有军民“反扫荡”、打游击足迹的印记;我看懂了故乡的水,水中荡漾着百姓送子送郎打日本的往事涟漪;我寻到了父辈们不怕牺牲、义无反顾的战斗精神;我理解了父亲对我的良苦用心。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父亲战斗过的地方入了党,两次出席全省先进模范代表大会,并实现了我的军营梦,从沂蒙山走进了军旅。之后,又实现了父亲的梦想,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2020年9月30日夜晚,我推着轮椅上的父亲,走在医院的桂花树下,皎洁的月光照在父亲苍老的脸庞上,看着父亲脖子上补了又补的衣领,回想着我和父亲的点点往事,想起我从家庭迈向社会的前夜,我问父亲,“还记得46年前我下乡的前夜,您给我的那张老照片和3张北海币吗?”父亲说:“当然记得。照片上的时维春和李尊宇牺牲了。那3张北海币可是宝贝呀,你别弄丢了。”说着,父亲又唱起他自己改编的歌:“我们在沂蒙山上……”我对父亲说:“您把太行山改成沂蒙山,什么是沂蒙精神啊?”他脱口而出:“艰苦奋斗!”
近年来,父亲的记忆力衰退得厉害,亲人的事情他总忘,但他没有忘记70多年前牺牲战友的名字,没有忘记沂蒙精神。父亲文化不高,但他用自己特殊的方式,为我们的人生把舵,用他爱的力量把一家三代聚齐在党旗下,成为党员之家。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参谋部某部退休干部)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