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怀念我的老师柏庆禹
发稿时间:2020-09-10 19:05:00 来源: 中国青年杂志
我的老师柏庆禹去世了。他殁于2020年9月4日17时,离第36个教师节只差6天。
柏老师是我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班主任。在我的求学生涯里,他是第一个懂我的人。
想来,人不可能自己了解自己,一个人要知道自己,总要借助外界的评价。但是,人们却又总是以为:外界对自己的理解存在偏差,即以为别人不可能真正懂自己——这正如,没有人怀疑自己的脸的存在,但恐怕没有谁真正见过自己的脸和后背。一个人要看到自己的脸,只能借助于镜子,但是,镜子里的脸,未必就是你的脸,因为镜子里的脸,起码是左右颠倒的,因此,一旦“照照镜子,红红脸”,人们就会觉得不自在,因为你会发现镜子和照片里的你,与你的自我评估有偏差。
知彼难,知己更难——人生一世,能遇到一个懂你的人,算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今天,一个懂我的人走了,我因此而感到了难忍的痛。我想写一些话,但是很难。

柏庆禹老师(左) 图片源自网络
1
我想到了自己的人生,奇怪于我怎么成了北大中文系的教师,而且,我怎么就成了一个“非典型”的中文系教师?想来想去,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遇到了他,遇到了我的柏老师。
从1978年秋天到1981年秋天,柏庆禹老师教了我三年,从初二到高二,他都是我的班主任。
在遇到柏老师之前,我喜欢的是数学,小学、初中时代,我不大看得起语文,而当时一般的定见也是如此——学生最不务正业的事就是看小说,人们常以为——世界上最没用的是语文和文学,以至于今天很多人还是认为:中文系,乃是北大最容易混的专业。
初中时代的某一个暑假,我沉迷于一本叫《许莼舫初等几何四种》的书,当时老师们说我聪明,无非就是因为我很擅长解几何题。
可惜这聪明没能持续多久,因为对数学的热爱,使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极大的困惑——即一切推演,并不是为了追求什么“未解之谜”,而只不过是为了证明早已存在的“前提”和“法则”而已。
及至学到代数,我的困惑就几乎发展为了绝望,我甚至感到:所谓代数者,无非是一种不断回到前提的循环论证而已——从此以后,直到今日,我便对我所曾经热衷的数学有所怀疑——所谓数学、所谓解题,无非就是永无止境地强化对于“规则”的确认,而这些规则,是人们事先知道、早就知道了的。
有谁家的孩子,是突然从聪明堕入愚蠢,由好学变为“厌学”的呢?在我看来,这如果不是因为遭遇到了什么外在特别的变故,那很可能是因为:这孩子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他不该想、也最终想不明白的事——易而言之,这孩子“想太多了”,而他想到的问题,可能在既定的规范里没有答案,因此从既定规范的角度看,也是根本上解决不了的。
于是,在大多数家长和老师看来,孩子喜欢胡思乱想,这起码就算是“不专心”,所谓“不专心”者,乃是孩子身上坏的根苗,这是将来“一事无成”的先兆。孩子倘若从小不专心,那将来要“废了”几乎是无疑的了。因此,教育工作的要义,就是要从“专心”入手,从纪律出发,为的就是废掉孩子的“胡思乱想”。
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第一考虑,恐怕还不是思想和知识,而是“严厉制止胡思乱想”,换句话说,教育首先是“规范”训练的场域。课堂,之所以不是可以随便提问的地方,就在于规范的教育,必须制止胡思乱想。
我的小学和中学分别上了四年,在今天看来,这种“八年制”的教育,当然是“不完善”的,而我就是这种“不规范教育”的产物。
记得有一回,我在数学课上提问说:“我见过锅、见过球、见过正月十五的月亮,就是没见过什么是‘圆’,数学教的东西,包括圆——统统都是不存在的。”
数学老师愣了几秒钟,然后直截了当地说——你脑子蠢得像头驴,再捣乱,你就给我出去。
我的同学们放声大笑,我被自己的这种“错误认识”吓坏了,而从此后,我不但对于数学,而且对于“学习”也丧失了兴趣。到了初二,我的成绩就一落千丈,在老师和同学眼里,我确实就是一头蠢驴。
今天看来,胡思乱想,当然不等于错误的思想;胡思乱想,无非是没有边界和规范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胡思乱想——这是孩子的本能,也是人的一种能力,如果教育的目的,就是把胡思乱想,统统变成规范地思想,倘若搞到极端,必定就会毁掉人的想象力。
当年,少不更事的我,就曾经差一点被这样“废掉”了,而我没有被废掉,就多亏了柏庆禹老师。
柏老师是在初二下学期,开始担任我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的,而如今想来,第一个指出我不是“一头蠢驴”的人,就是我的语文老师——我中学时代的班主任柏庆禹,起因则是我的一篇作文《运动会》。
在那次学校的运动会上,我的工作是帮助参赛的选手保管他们换下来的衣服,而柏老师在讲评大家的作文时,破天荒地把我的文章挑出来,仔细地讲评了半节课。
他这样说:“在运动会上,一般只有两种人、两个视角,一个是观众视角,一个是运动员视角,而这篇作文的‘奇特’之处在于:从另外一个特殊的视角(保管衣服者)出发,把上述两种不同的视角沟通起来,这样一来,也就沟通了场内与场外,台上和台下。”
他接着说:“作者的可贵,就在于‘观察角度的独特’,因此,能够从‘个别’去表现一般,能够置身事外,又投入其中——而这样的态度叫‘鉴赏’,这样的能力叫审美,这样的作品叫艺术。”
他还说,“文似看山不喜平”,艺术的根源就在于“奇思妙想”。
令我终生难忘的是,柏老师讲到这里的时候,顿了一下,然后,方才徐徐地说:“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在别处,就在于四个字——解放思想!”
那一天,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被数学老师严厉禁止的“胡思乱想”,还可以被称为“奇思妙想”;那一天,我第一次知道:知识不等于规范,因为知识发展的根本动力,就在于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不能用条条框框去束缚人们的思想。
那一天,我第一次知道:看世界、看事物不仅有一个视角,而是有多个视角,从多个视角看世界,叫审美,叫鉴赏,叫“批判”;那一天,我第一次知道——人身上有一种能力,使它区别于物,而人所具备的这种能力,就叫艺术能力。

而那一天,我的柏老师告诉我,我不是一头蠢驴,因为驴不具备想象力。正因为我身上具备着这样一种叫“想象力”的能力——所以我不是驴。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78年的秋天(因为那是在学校的秋季运动会结束之后),就是在那时,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有一位老人发表了一篇讲话,题目就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从哪里来,他就不知道往哪里去。我永远记得那个秋天,永远想念那个秋天,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成长的那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将会左右我的一生。
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遇到了一位好老师——我的语文老师、班主任柏庆禹。
今天,有人把那个时代叫作“怀疑的时代”,而我认为,此类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正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础上,方才形成了“振兴中华”的时代共识、全民共识。一如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方才形成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方才形成了那样一种历史的总体视野、那样一种生动磅礴的历史主旋律。
没有解放思想,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会有真正的团结一致向前看。
2
昨天,我问了我的博士后一个问题: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究竟有什么区别?
他想了很久,回答我说:新古典经济学是规范的、讲究形式的,而古典经济学则是不规范的,在形式上是不完善的。
我说:你讲得很对,但也不对。
因为在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时代,其实还没有所谓经济学这个学科。斯密原本是教文学的,《道德情操论》是一篇关于审美的著作。对主观判断力的研究,这是斯密思想的基础。而《国富论》,不过是他为了养家糊口,担任苏格兰海关税官后的产物。实际上,斯密并不相信经济学可以成为一个学科,更不必说,有朝一日成为比文学更伟大的学科。
李嘉图是个大财阀,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经济学家能赚到他那么多的钱,而在李嘉图看来,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门可以指导赚钱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看,所谓“经济学”作为一门指导赚钱的学问,完全不能成立。
马克思原本是一个法哲学家,而他就是从这个“外行”的视野出发,进入了政治经济学,最终,马克思构建了《资本论》的大厦。
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当然都不是没有学问的人,恰恰相反,他们的学问,是后来的经济学家无法比拟的,但是,他们都认识到:形式逻辑,特别是数学,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是一种严重的束缚。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经济学成为一个显赫的、规范性的学科的时候,当他采用了数学的思维的时候,它的生机与活力就丧失了,因为它不再能够直面现实问题,而堕入了对于自己设置的前提和假定的循环论证。
对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来说,“完善的形式”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荒谬的,形式逻辑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问题。因为马克思说过:“重要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表现时代精神最实际的呼声。”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回到斯密,这都意味着——不是从一个规定的、自我设定的前提出发,而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出发——这是一种能力。康德将它称为判断力,斯密把它称为“鉴赏”,而马克思则将其称为“批判”。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绝不意味着小说和诗歌,因为文学就意味着判断力、鉴赏力和批判的能力——而这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是知识发展的真正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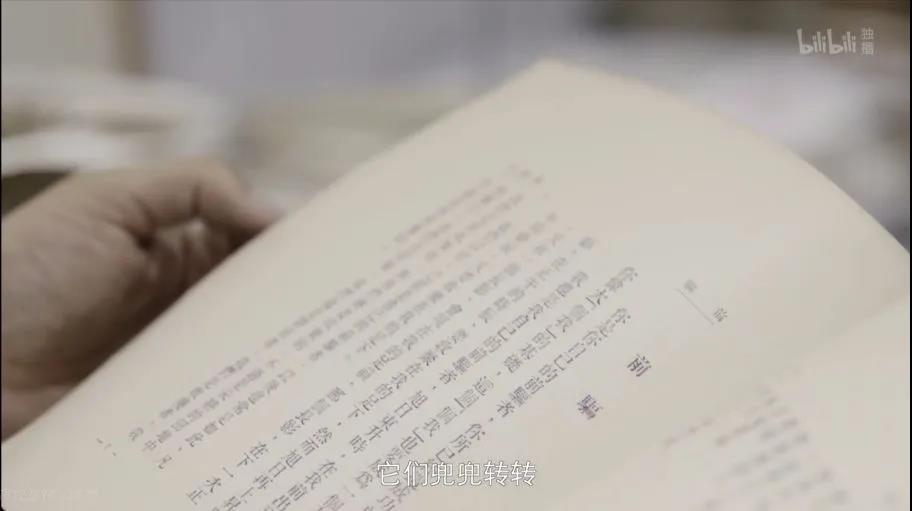
我的博士后问:“韩老师,您为什么想起来问我这个问题?今天,您为什么要给我讲起这个问题呢?”
我说:“因为今天,我的老师去世了,我想起他,心里很难过。正像我想起马克思、鲁迅的去世,总是感到非常难过。但是,我心里的话没有人可以讲,见到你,所以就讲了这样一些话,不管你爱听不爱听。”
我的博士后沉思了良久,说:“您的意思是——‘文学’已经去世了吗?”
我说:“不,因为我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审美、没有鉴赏、没有判断力、没有批判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世界?”
3
我经常考虑一些奇怪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人们为什么感念他们的老师。
我想,这大约是因为:老师教给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人、办事的“规则”和法则,因此,所谓的“好学生”者,总是守规矩,是对“规则”领会得快且好的那一种吧!
按照学来的规矩和规则去办事,而待出徒毕业之后,更能把此类“关于规矩的游戏”进行得更加得心应手,于是便因之出人头地——因此,我以为,他们的所谓“感谢师恩”者,实则不过是——感谢老师教给他们的规矩和“如何守规则”,乃至长大之后,如何去得心应手地钻规矩的空子——而此类所谓“感谢师恩”者,不过是表达对于规矩和法则的敬畏、五体投地、得心应手,且以此警戒后人而已。
教师节来了,如此感恩戴德的文章会多起来吧?
而我写不出这样的文章,因为此时此刻,那个懂我,因此我以为是我的老师的人死了,这使我反倒更加憎恨那些以尊师、重道之名,讴歌“规则”的文字。
在我的求学、学术生涯里,所最令人恐惧者,就是有人不去弘扬学术、弘扬知识,而是大力弘扬什么“学术规范”,而所谓“学术规范”者,往往为不学无术的“大佬们”所手订,凡符合其意志者,便符合规范,而他们的目的,无非是要造成一个没有知识、没有学术,只有所谓“规范”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们的理想,无非就是当个行会的头——以规范的名义。
4
人总是要死的,但是,我总是拒绝把这件事往身边的人那里去想,因为我的潜意识,是回避这件事的,在我的意识的深处,总是以为:他们会一直好好地在那里,即使遇到种种不虞和无常,他们也总是能够转危为安,就像噩梦醒来是早晨,就像太阳落下又照旧升起,正像无论经历了多大变故和灾难,生活最终会恢复常态——就像一切秋去,必是为了春来。
人人都知道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却总是“往好处去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死的否认本身,就是一种反常的视角,正如我们对于亲人的死的否认,那是一种亲人才有的不顾一切的视角,是一种不顾一切也要坚持下去的绝对个人的视角。
我想,这就是我的老师教给我的视角——因为他明明知道,我这样的落后青年不可能考上大学,但是,他却一直坚信我一定能考上大学,甚至能考上北京大学。他明明知道,我绝不是他的学生中最优秀的,但是他还是力排众议,让我回校代表优秀毕业生给学弟学妹们做报告。那次,他怕我紧张,就没有亲临现场,而是在场外听大喇叭里传出的我的信口开河、慷慨激昂。

他明明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去写毛泽东、马克思,但当我写的《重读毛泽东》出版后,他却仔仔细细读了几遍,在书页上做了密密麻麻的眉批,就像当年修改我的第一篇作文——最后,又在书的扉页上写了“角度好”三个字。
柏老师,您生病后,明明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却笑着对我说:“怎么就会死呢,你写的书,我还没看够……”
人总是要死的,这也许算是公理吧!但我的老师却告诉我们:一定要好好地、认真地、坚定地、不屈不挠地活着,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一切苦难都会过去的,最终,我们每个人都会好好的、永远在一起,直到地老天荒,还是在一起……
我想,这就是文学吧!这就是您教给我的文学吧!这就是您讲给我们的一个美丽的故事,它把生活变成了传奇,正如老师——当年的您——把一道道难题变成了乐趣。
亲爱的老师,我感谢您在我少不更事的时候,在我厌弃了知识和学习——乃至厌弃了生活的时候,把我厉声唤醒,感谢您把弱小的我,高高地举起。您像点火一样,点燃、培养、壮大了我的想象力,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能力,才能使我今天能够蔑视包括人人必死在内的所谓“公理”,才使我能够坚信——您一直活在我的精神的世界里,而随着那个世界的不断壮大,您也必将变得更加生动、更加健康、更加深刻,更加栩栩如生,更加像我想象的您。
亲爱的老师,衷心地谢谢您——这句话——这么久啦,竟然一直没有来得及告诉您……

作者:韩毓海
来源:《中国青年》杂志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